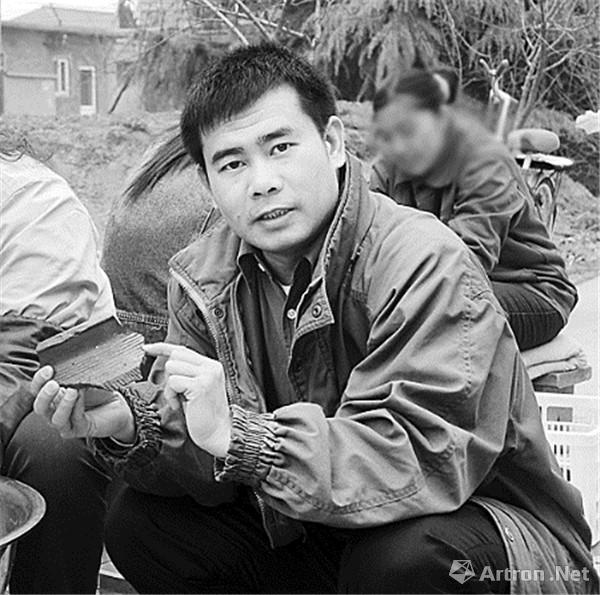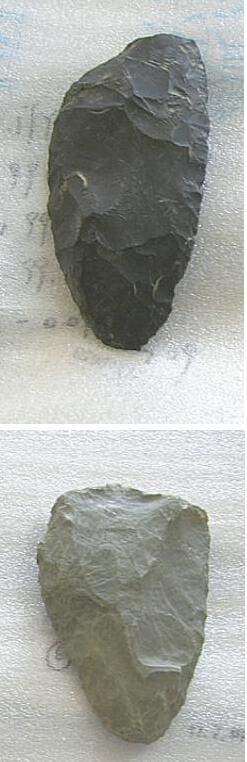去年年底,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徐旭生著、罗宏才注释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样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中国考古学开创者之一的苏秉琦先生之子苏恺之先生有感而发,回忆了作为自己父亲多年的老师、同事和挚友,自己眼中亲切的徐老伯的点滴往事,深切缅怀徐旭生先生这位学术大家。

▲徐旭生、苏秉琦等人在宝鸡“古大散关”的合影(摘自《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说起徐老伯,我有着难以割舍的思念和崇敬之情,也有许多可述说的往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家和我家也曾是紧密的邻居。在刚刚到来的2018年——他130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愿给出几件值得回味的旧事。
“莫怕,这里的泥土不脏”
1941年秋,母亲带着我从北平奔波了一个多月,终于来到了昆明北郊的黑龙潭,和父亲团聚了。我们的新居安顿好后没多久,大概是个星期日吧,徐老伯就来探望我们。随后,三个大人拉着四岁的我,到山后的几个小山坡观看,我依稀记得这位留着长胡子的老者很健谈,主要是向父亲说什么,声音郎朗,有时也特地对母亲指点着说一些,例如龙云家族祖坟地的典故什么的。
有个小场景却让我颇有印象并记忆至今。我们在山上走到一个坡地,长有松树,不很茂密,有阳光也有树荫,很适合休息。他们席地而坐,我依旧四处玩耍,这时徐老伯拉住我的手说:“小苏,坐在这里吧。”我没这种坐地的思想准备,有些迟疑,徐老伯又接着说:“莫怕,这里的泥土不脏,就躺在这里吧,很舒服的。”
我能记得这个瞬间,是因为我第一次在室外而且是在四处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清静环境里,竟然在一位陌生老者的鼓励下,躺在了这有些温暖的土地上。秋天的阳光散发着暖意,的确舒适,我还闻到了轻微的松针特有的清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奇异感受。过了十年之后,在我阅读了徐老伯的西游日记后,得知了他的奇特探险经历时,又加深了对他说的“莫怕,土地不脏”几个字的理解,让我不断体味着其中的含义,懂得了他愿意植根于底层,注重走访调查,是位接地气的人。这既影响着我的父亲,也自然地滋润了我的成长。
我们家于1948年搬到了当时的西直门大街26号,不久后,徐老伯一家也搬来了这个大院,解放后这里是“中国科学院第二宿舍”。自此,我们两家来往紧密,母亲和徐伯母更是无话从不说,亲似姐妹。一次徐伯母来我家和母亲聊天,说起那次到山上观光的事,我才知道,那天徐老伯曾在我家吃了便饭。母亲说:“提起这事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那时我刚来昆明,不熟悉使炭火炉子,又是临时的任务,我做的菜、汤、米饭都不怎么像样,我对你家徐老说做的饭真有些不像样,可徐先生边吃边说:‘很好嘛,这就很好了’,他真是位干大事而不重琐碎小事的人。”
《西游日记》成了我少年时代的耀眼读物
1951年暑假,父亲拿给我两大本书,作为我的课外读物,重点是《徐旭生西游日记》,再辅助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十四五岁的我起初只是对照片有兴趣 ,晚上再经父亲的解说,也让我加深了理解,有些情节也值得品味,直到现在我还能说出一些。
接着父亲要我细读文字,我就觉得没味道了,那时在文字里许多地名都是只标注了旧式的汉语拼音,让我头疼。于是父亲就想了个办法:陆续出了许多小思考题,让我在文字堆中找寻答案,例如他们的喝水难关怎么解决的?怎么填饱肚子的?怎样克服天冷地冻?晚间能干什么?我写出答案,母亲也常来议论,让我第一次阅读和体会了这个老人的经历,也激发了我对那些神奇经历的兴趣。暑假过去,自己也感觉变得聪明了些,感觉我的眼光也有了变化,重新端详这位可亲的老者,有种莫名的崇拜感:他目光有神、精神矍铄,说话头头是道。“这个大学校长(徐旭生曾于1931-1932年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就是不简单,真棒!”。我还联想到日记里写到的、也曾来过我家做客、身体并不粗壮的黄文弼伯伯,原来他还做了很有英勇气魄的事迹,也很值得尊敬。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徐老伯的仰慕之情不断加深,也开始做多角度的思考。上高中时,我忽而有了一个怪想法:学校里的政治课讲述了长征,还邀请了老红军来做报告,场面热烈,那么,“要是请徐老伯、黄文弼伯伯来作报告,讲西北考察和历险,效果也会很棒的吧?”我父亲回答说,在很多方面都不要把科学考察和历史性的伟大长征相比拟。当然那次艰难困苦的考察,毕竟是我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加的合作科学考察:那时的中外双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提供经费的外国财团自然有其利益目的,而我国的学者在维护国家权益的同时,则是要把我们国土上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调查清楚,成为开端,是很可敬的。
现今,徐老伯的《陕西考古日记》出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过去我们对那次既轰轰烈烈又默默无闻的陕西考古调考察忽略和淡忘了。我们现在对徐老伯有了重新的全方位评价和认识,我很欣慰。我要说一句话:我们对徐老的评价和认识,似乎都可以在这个七八十年前的日记里找到一些苗头或雏形。
“小苏很好呀,他敢于独自和大人交往啦!”
我1952年进入高中,许多同学都在集邮,我也加入了,而且我利用父亲来往信件较多的优势,集邮量已属上游,但还不满足。我忽然想到了徐老伯:“他在困苦的野外条件下都坚持写信,现在肯定有很多收信吧!”。一天我在大院里玩耍时碰见徐老伯下班回来,立刻鼓起勇气迎了上去:“徐老伯,我正在集邮,已经有一百多张,请您帮助我攒几张吧,最好是纪念邮票。”徐老伯停下了步子,望着我迟疑了一会儿,轻声念叨:“哦,邮票,纪念邮票。好,这样子,我过些天再回答你吧。”
我内心忐忑,觉得平生第一次大胆的试探竟然落了空,有些灰心。又想:这个事儿绝不可告诉父母,免得丢脸,还受责怪。过了些日子,我差不多忘了这件事情。一天又碰上徐老伯,他含笑招呼我说:“就在这个信袋子里装着呢。有一张小号的方形邮票,它不是纪念邮票,却是少有的‘大清国邮政龙票’。”
几日里我常摆弄它,把这张龙票专门安排在集邮册的第一页,这个行动被母亲看见了,问我哪里来的这张稀有邮票,我只得如实招供。母亲听了倒也没说什么,我总算放了心。可又过了几天吧,母亲对我说,以后有啥想法先和他们说说,商量一下多好。我明白了,准保是他们议论了我的秘密,那就等着父亲的批评吧,但是父亲没有和我说这事,我心里慢慢地放松了。可又过了些日子,父亲下班回来笑着大声对我和母亲说:“徐老伯可是表扬了你一番呢 。他说小苏长大了,像个半大人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敢于和大人交谈,有出息”。父亲还说:“我也为你高兴,爸爸该表扬你!”
再过了些时日,母亲才私下对我说:“徐老伯可是把你要邮票的事认真对待的,以后不可这样随便麻烦人家了,他比你爸忙多了。”我这才慢慢觉得,父亲有意地把一部分要说的话留存了些日子,再由妈妈的口传递给我的。
我还逐渐意识到,父亲在和徐老伯的常年接触中,也接受了不少徐老伯关于青少年培养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作为教育家,徐老伯对于青少年的培育自有他一些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他也肯定向父亲说过许多。记得多年后,我从徐伯母和母亲的家常话里知道了,她俩对于两个家庭孩子的培养都是满意的。徐伯母对母亲说:“咱们的孩子都能自觉走上正道,咱们都没分心费力,都算是‘精忠报国’了吧。”
在我成年后又体悟到,两个家庭培育孩子的共同点,就是教导孩子老实做人,以及家庭里始终如一的学习读书气氛。
那枚“大清国邮政龙票”,我已经传给了我的儿子,并告诉他:“要记住徐旭生——他是你爷爷的老师!”
大智若愚——“他可绝不是书呆子!”
我上大学后的1957年初冬,徐老伯经过努力进步,光荣入党了。这个喜讯在宿舍大院里也传开来。这时我越发感觉到,父亲在几次运动中都显得“落后”,这让我思考更多的问题。
1958年春节,大年初一那天,所有上班的职工集合起来做了团拜就算拜年了。我遇到了冯家升伯伯的儿子,他和我是同龄人,一起说起了父辈人的思想进步问题。他觉得他的父亲很像徐老伯,也是书呆子也要求进步,入党,但不被人接受。我俩还谈到对徐老伯入党的事在大院里的那些小议论。
我把这些消息告诉了父亲:“听说,积极要求进步的徐老伯有些书生气,是个书呆子,像老学究——头脑里都是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父亲听了很不认同,说了一大串话:“书呆子?绝不是,他头脑灵活着呢。他读的书可真是不少,知识渊博,见识也多,通晓古今中外。他才不是脱离实际呢,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积极作用不可抹杀,这样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他是一贯提倡理论结合实际,说他是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那还差不多呢。”
此后,父亲又陆续地补充说给我许多认识,例如他说:“你懂吗?大智若愚,许多人不懂。凡成大器者,眼睛不喜欢盯着看那些区区小事,这反倒会让小气的人看着他不理解了。你也要注意审视你自己,是不是你已经成为了‘小人之心’了,才会误以为人家是书呆子了”。又说:“大智者,常有大爱,而不是拘泥于小爱,这会让一些人不理解,以为他像傻子那般不懂得爱自己爱小家,其实人家很爱国、很爱我们民族,这就是人家的思想境界。”父亲还告诉我:“五四运动后涌现出来的杰出文人学者,都有一股子死不回头的傻劲,都是个性、棱角鲜明的人。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人,重视、培养得太少了。”
“他可是位连鲁迅都没有说过不字的人!”
文革一开始,徐老伯就被批斗。
1967年秋,父亲突然对我说:“等这个星期日,你一个人去一趟徐老伯家吧,他好多天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这真让人挂念。”我很懂得,父亲的这一安排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的,因为那时进出入宿舍大门都要经过红卫兵的查问,登记姓名、出身、单位。如有异常就很麻烦。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还要求我去,必定有父亲的考虑。
我来到建国门大街,马路上全是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和卡车,车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语录歌曲,和“打倒一切反动派!”口号。我绕过了红卫兵的看守后来到徐老伯家。徐老伯半躺在床上正在看书,豁然见到了我很感意外和喜悦。但我明显感到,他的气色不太好,说话声音也弱了许多,略带沙哑,我心头一阵疼痛,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我说明来意,向徐老伯和徐伯母介绍了父亲的近期情况,又聊了几句家常。我想不宜停留过久,就准备告辞。不想他立即要我协助他,从他床下拿出了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问道:“知道井冈山会师吧?”之后说,他在庐山休假之后绕道去了井冈山,走访了当地的一些老者。“写兵家的传记和历史,要拿着时间的和空间的两把尺子做描述”。他的声音似乎又鲜亮了许多。我听着有些担心,觉得这个话题和外面的大环境反差太大了,但我不便打断。他说他走访了当地的老者,一一作了笔录,得到了许多鲜活的历史资料。接着又打开了一张用毛笔绘制的示意地图,标明了几支队伍的行进路线——根据地的诞生史料呈现了出来。这个瞬间让我终身铭记,让我看到了,他是位唯物者,是位追求真善美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
我再次告辞,徐老伯却又想起一件事,要把他珍藏了三十多年的,我父亲1935年春节期间奉他之命到宝鸡附近做考察报告信函,返还到我父亲手中,“也算是一个纪念吧。”
我急忙回家,向父母讲述了这些。父亲也很有感触和伤感,又说了些在宝鸡的旧事。父亲觉得,这次徐老伯这么急切要和我讲述他的井冈山之行,要把他的纪念物返还给他,似乎是觉得未来的日子不长了,一定要把重要的东西留在世上。“真让人揪心啊!”那时,我们都很无奈。
多年之后,父亲才和母亲说起,那次派我前往徐老伯家,是在徐老伯被批斗之后。那天要他站到桌上的一个凳子上,完全是人格侮辱。徐老伯提出抗议,立刻挨了拳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随后多日没来上班,心痛的父亲才决定要我去探望。父亲对我母亲说:“这群王八犊子、败类,太不像话了!竟然如此欺辱批斗他,太过分了!这可是曾和李大钊、鲁迅一起共事战斗过的人,连鲁迅都不曾说过他一个不字的人,他们不是人,更没资格评论别人!”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骂出“王八犊子”这四个字。
一颗巨星落下了
1969年,我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住进研究所里,住通板铺,过军事化生活,那是一段心力交瘁的日子。而徐老伯也倒下了,住进了医院,师生二人相距几百米却不能相见。自此,徐老伯的体质和精神每况愈下。1976年1月,徐老伯去世了,无声无息。父亲很难受却不愿提及,我们也难做什么。母亲对我们说,沉默就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了,家里人谈论了许多,父亲又说起了徐老伯:“可惜了,徐公不在了,不然他也会像当年打败了日本鬼子时的那股子高兴劲儿,我还能再次听到他的高谈阔论,那该多好啊!”
我对父亲说的“高谈阔论”,有很深的印象。我和父母再次回忆起了那个难忘的胜利时分。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后,学校空前地不讲课文了,而是布置了家庭作业——和家人一起糊制一个灯笼。
我回家向妈妈要了钱,买好红纸,就又出门玩耍去了。过了一会儿,也不知怎么地,我忽而想:何不去父亲办公地玩玩?就从黑龙潭跑到几公里之外的落索坡(那时徐老伯和父亲迁移到了这里上班)。只见屋子里有好几个人坐着,唯独徐老伯站着走动,他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半举起,食指在半空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说,振振有词,大家都很兴奋。
徐老伯在谈论着什么?当时我不懂,也就不曾记得,但他神采奕奕的英姿,深深地浇铸在我的心里。直到今日每每想起,我总会觉得,他讲话的核心应该是:“果不出我之所料!”
如果我是位雕像师,我一定要为徐老伯雕刻一尊这样的塑像。
这就是我敬仰的徐老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的徐旭生先生!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9日第7版)

▲徐旭生、苏秉琦等人在宝鸡“古大散关”的合影(摘自《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说起徐老伯,我有着难以割舍的思念和崇敬之情,也有许多可述说的往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家和我家也曾是紧密的邻居。在刚刚到来的2018年——他130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愿给出几件值得回味的旧事。
“莫怕,这里的泥土不脏”
1941年秋,母亲带着我从北平奔波了一个多月,终于来到了昆明北郊的黑龙潭,和父亲团聚了。我们的新居安顿好后没多久,大概是个星期日吧,徐老伯就来探望我们。随后,三个大人拉着四岁的我,到山后的几个小山坡观看,我依稀记得这位留着长胡子的老者很健谈,主要是向父亲说什么,声音郎朗,有时也特地对母亲指点着说一些,例如龙云家族祖坟地的典故什么的。
有个小场景却让我颇有印象并记忆至今。我们在山上走到一个坡地,长有松树,不很茂密,有阳光也有树荫,很适合休息。他们席地而坐,我依旧四处玩耍,这时徐老伯拉住我的手说:“小苏,坐在这里吧。”我没这种坐地的思想准备,有些迟疑,徐老伯又接着说:“莫怕,这里的泥土不脏,就躺在这里吧,很舒服的。”
我能记得这个瞬间,是因为我第一次在室外而且是在四处没有任何其他人的清静环境里,竟然在一位陌生老者的鼓励下,躺在了这有些温暖的土地上。秋天的阳光散发着暖意,的确舒适,我还闻到了轻微的松针特有的清香,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奇异感受。过了十年之后,在我阅读了徐老伯的西游日记后,得知了他的奇特探险经历时,又加深了对他说的“莫怕,土地不脏”几个字的理解,让我不断体味着其中的含义,懂得了他愿意植根于底层,注重走访调查,是位接地气的人。这既影响着我的父亲,也自然地滋润了我的成长。
我们家于1948年搬到了当时的西直门大街26号,不久后,徐老伯一家也搬来了这个大院,解放后这里是“中国科学院第二宿舍”。自此,我们两家来往紧密,母亲和徐伯母更是无话从不说,亲似姐妹。一次徐伯母来我家和母亲聊天,说起那次到山上观光的事,我才知道,那天徐老伯曾在我家吃了便饭。母亲说:“提起这事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那时我刚来昆明,不熟悉使炭火炉子,又是临时的任务,我做的菜、汤、米饭都不怎么像样,我对你家徐老说做的饭真有些不像样,可徐先生边吃边说:‘很好嘛,这就很好了’,他真是位干大事而不重琐碎小事的人。”
《西游日记》成了我少年时代的耀眼读物
1951年暑假,父亲拿给我两大本书,作为我的课外读物,重点是《徐旭生西游日记》,再辅助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十四五岁的我起初只是对照片有兴趣 ,晚上再经父亲的解说,也让我加深了理解,有些情节也值得品味,直到现在我还能说出一些。
接着父亲要我细读文字,我就觉得没味道了,那时在文字里许多地名都是只标注了旧式的汉语拼音,让我头疼。于是父亲就想了个办法:陆续出了许多小思考题,让我在文字堆中找寻答案,例如他们的喝水难关怎么解决的?怎么填饱肚子的?怎样克服天冷地冻?晚间能干什么?我写出答案,母亲也常来议论,让我第一次阅读和体会了这个老人的经历,也激发了我对那些神奇经历的兴趣。暑假过去,自己也感觉变得聪明了些,感觉我的眼光也有了变化,重新端详这位可亲的老者,有种莫名的崇拜感:他目光有神、精神矍铄,说话头头是道。“这个大学校长(徐旭生曾于1931-1932年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就是不简单,真棒!”。我还联想到日记里写到的、也曾来过我家做客、身体并不粗壮的黄文弼伯伯,原来他还做了很有英勇气魄的事迹,也很值得尊敬。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徐老伯的仰慕之情不断加深,也开始做多角度的思考。上高中时,我忽而有了一个怪想法:学校里的政治课讲述了长征,还邀请了老红军来做报告,场面热烈,那么,“要是请徐老伯、黄文弼伯伯来作报告,讲西北考察和历险,效果也会很棒的吧?”我父亲回答说,在很多方面都不要把科学考察和历史性的伟大长征相比拟。当然那次艰难困苦的考察,毕竟是我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加的合作科学考察:那时的中外双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提供经费的外国财团自然有其利益目的,而我国的学者在维护国家权益的同时,则是要把我们国土上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调查清楚,成为开端,是很可敬的。
现今,徐老伯的《陕西考古日记》出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过去我们对那次既轰轰烈烈又默默无闻的陕西考古调考察忽略和淡忘了。我们现在对徐老伯有了重新的全方位评价和认识,我很欣慰。我要说一句话:我们对徐老的评价和认识,似乎都可以在这个七八十年前的日记里找到一些苗头或雏形。
“小苏很好呀,他敢于独自和大人交往啦!”
我1952年进入高中,许多同学都在集邮,我也加入了,而且我利用父亲来往信件较多的优势,集邮量已属上游,但还不满足。我忽然想到了徐老伯:“他在困苦的野外条件下都坚持写信,现在肯定有很多收信吧!”。一天我在大院里玩耍时碰见徐老伯下班回来,立刻鼓起勇气迎了上去:“徐老伯,我正在集邮,已经有一百多张,请您帮助我攒几张吧,最好是纪念邮票。”徐老伯停下了步子,望着我迟疑了一会儿,轻声念叨:“哦,邮票,纪念邮票。好,这样子,我过些天再回答你吧。”
我内心忐忑,觉得平生第一次大胆的试探竟然落了空,有些灰心。又想:这个事儿绝不可告诉父母,免得丢脸,还受责怪。过了些日子,我差不多忘了这件事情。一天又碰上徐老伯,他含笑招呼我说:“就在这个信袋子里装着呢。有一张小号的方形邮票,它不是纪念邮票,却是少有的‘大清国邮政龙票’。”
几日里我常摆弄它,把这张龙票专门安排在集邮册的第一页,这个行动被母亲看见了,问我哪里来的这张稀有邮票,我只得如实招供。母亲听了倒也没说什么,我总算放了心。可又过了几天吧,母亲对我说,以后有啥想法先和他们说说,商量一下多好。我明白了,准保是他们议论了我的秘密,那就等着父亲的批评吧,但是父亲没有和我说这事,我心里慢慢地放松了。可又过了些日子,父亲下班回来笑着大声对我和母亲说:“徐老伯可是表扬了你一番呢 。他说小苏长大了,像个半大人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敢于和大人交谈,有出息”。父亲还说:“我也为你高兴,爸爸该表扬你!”
再过了些时日,母亲才私下对我说:“徐老伯可是把你要邮票的事认真对待的,以后不可这样随便麻烦人家了,他比你爸忙多了。”我这才慢慢觉得,父亲有意地把一部分要说的话留存了些日子,再由妈妈的口传递给我的。
我还逐渐意识到,父亲在和徐老伯的常年接触中,也接受了不少徐老伯关于青少年培养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作为教育家,徐老伯对于青少年的培育自有他一些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他也肯定向父亲说过许多。记得多年后,我从徐伯母和母亲的家常话里知道了,她俩对于两个家庭孩子的培养都是满意的。徐伯母对母亲说:“咱们的孩子都能自觉走上正道,咱们都没分心费力,都算是‘精忠报国’了吧。”
在我成年后又体悟到,两个家庭培育孩子的共同点,就是教导孩子老实做人,以及家庭里始终如一的学习读书气氛。
那枚“大清国邮政龙票”,我已经传给了我的儿子,并告诉他:“要记住徐旭生——他是你爷爷的老师!”
大智若愚——“他可绝不是书呆子!”
我上大学后的1957年初冬,徐老伯经过努力进步,光荣入党了。这个喜讯在宿舍大院里也传开来。这时我越发感觉到,父亲在几次运动中都显得“落后”,这让我思考更多的问题。
1958年春节,大年初一那天,所有上班的职工集合起来做了团拜就算拜年了。我遇到了冯家升伯伯的儿子,他和我是同龄人,一起说起了父辈人的思想进步问题。他觉得他的父亲很像徐老伯,也是书呆子也要求进步,入党,但不被人接受。我俩还谈到对徐老伯入党的事在大院里的那些小议论。
我把这些消息告诉了父亲:“听说,积极要求进步的徐老伯有些书生气,是个书呆子,像老学究——头脑里都是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父亲听了很不认同,说了一大串话:“书呆子?绝不是,他头脑灵活着呢。他读的书可真是不少,知识渊博,见识也多,通晓古今中外。他才不是脱离实际呢,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积极作用不可抹杀,这样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他是一贯提倡理论结合实际,说他是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那还差不多呢。”
此后,父亲又陆续地补充说给我许多认识,例如他说:“你懂吗?大智若愚,许多人不懂。凡成大器者,眼睛不喜欢盯着看那些区区小事,这反倒会让小气的人看着他不理解了。你也要注意审视你自己,是不是你已经成为了‘小人之心’了,才会误以为人家是书呆子了”。又说:“大智者,常有大爱,而不是拘泥于小爱,这会让一些人不理解,以为他像傻子那般不懂得爱自己爱小家,其实人家很爱国、很爱我们民族,这就是人家的思想境界。”父亲还告诉我:“五四运动后涌现出来的杰出文人学者,都有一股子死不回头的傻劲,都是个性、棱角鲜明的人。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人,重视、培养得太少了。”
“他可是位连鲁迅都没有说过不字的人!”
文革一开始,徐老伯就被批斗。
1967年秋,父亲突然对我说:“等这个星期日,你一个人去一趟徐老伯家吧,他好多天没来上班,据说是病了,这真让人挂念。”我很懂得,父亲的这一安排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的,因为那时进出入宿舍大门都要经过红卫兵的查问,登记姓名、出身、单位。如有异常就很麻烦。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还要求我去,必定有父亲的考虑。
我来到建国门大街,马路上全是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和卡车,车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语录歌曲,和“打倒一切反动派!”口号。我绕过了红卫兵的看守后来到徐老伯家。徐老伯半躺在床上正在看书,豁然见到了我很感意外和喜悦。但我明显感到,他的气色不太好,说话声音也弱了许多,略带沙哑,我心头一阵疼痛,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我说明来意,向徐老伯和徐伯母介绍了父亲的近期情况,又聊了几句家常。我想不宜停留过久,就准备告辞。不想他立即要我协助他,从他床下拿出了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问道:“知道井冈山会师吧?”之后说,他在庐山休假之后绕道去了井冈山,走访了当地的一些老者。“写兵家的传记和历史,要拿着时间的和空间的两把尺子做描述”。他的声音似乎又鲜亮了许多。我听着有些担心,觉得这个话题和外面的大环境反差太大了,但我不便打断。他说他走访了当地的老者,一一作了笔录,得到了许多鲜活的历史资料。接着又打开了一张用毛笔绘制的示意地图,标明了几支队伍的行进路线——根据地的诞生史料呈现了出来。这个瞬间让我终身铭记,让我看到了,他是位唯物者,是位追求真善美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
我再次告辞,徐老伯却又想起一件事,要把他珍藏了三十多年的,我父亲1935年春节期间奉他之命到宝鸡附近做考察报告信函,返还到我父亲手中,“也算是一个纪念吧。”
我急忙回家,向父母讲述了这些。父亲也很有感触和伤感,又说了些在宝鸡的旧事。父亲觉得,这次徐老伯这么急切要和我讲述他的井冈山之行,要把他的纪念物返还给他,似乎是觉得未来的日子不长了,一定要把重要的东西留在世上。“真让人揪心啊!”那时,我们都很无奈。
多年之后,父亲才和母亲说起,那次派我前往徐老伯家,是在徐老伯被批斗之后。那天要他站到桌上的一个凳子上,完全是人格侮辱。徐老伯提出抗议,立刻挨了拳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随后多日没来上班,心痛的父亲才决定要我去探望。父亲对我母亲说:“这群王八犊子、败类,太不像话了!竟然如此欺辱批斗他,太过分了!这可是曾和李大钊、鲁迅一起共事战斗过的人,连鲁迅都不曾说过他一个不字的人,他们不是人,更没资格评论别人!”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骂出“王八犊子”这四个字。
一颗巨星落下了
1969年,我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住进研究所里,住通板铺,过军事化生活,那是一段心力交瘁的日子。而徐老伯也倒下了,住进了医院,师生二人相距几百米却不能相见。自此,徐老伯的体质和精神每况愈下。1976年1月,徐老伯去世了,无声无息。父亲很难受却不愿提及,我们也难做什么。母亲对我们说,沉默就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了,家里人谈论了许多,父亲又说起了徐老伯:“可惜了,徐公不在了,不然他也会像当年打败了日本鬼子时的那股子高兴劲儿,我还能再次听到他的高谈阔论,那该多好啊!”
我对父亲说的“高谈阔论”,有很深的印象。我和父母再次回忆起了那个难忘的胜利时分。传来了胜利的消息后,学校空前地不讲课文了,而是布置了家庭作业——和家人一起糊制一个灯笼。
我回家向妈妈要了钱,买好红纸,就又出门玩耍去了。过了一会儿,也不知怎么地,我忽而想:何不去父亲办公地玩玩?就从黑龙潭跑到几公里之外的落索坡(那时徐老伯和父亲迁移到了这里上班)。只见屋子里有好几个人坐着,唯独徐老伯站着走动,他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半举起,食指在半空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说,振振有词,大家都很兴奋。
徐老伯在谈论着什么?当时我不懂,也就不曾记得,但他神采奕奕的英姿,深深地浇铸在我的心里。直到今日每每想起,我总会觉得,他讲话的核心应该是:“果不出我之所料!”
如果我是位雕像师,我一定要为徐老伯雕刻一尊这样的塑像。
这就是我敬仰的徐老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的徐旭生先生!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9日第7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