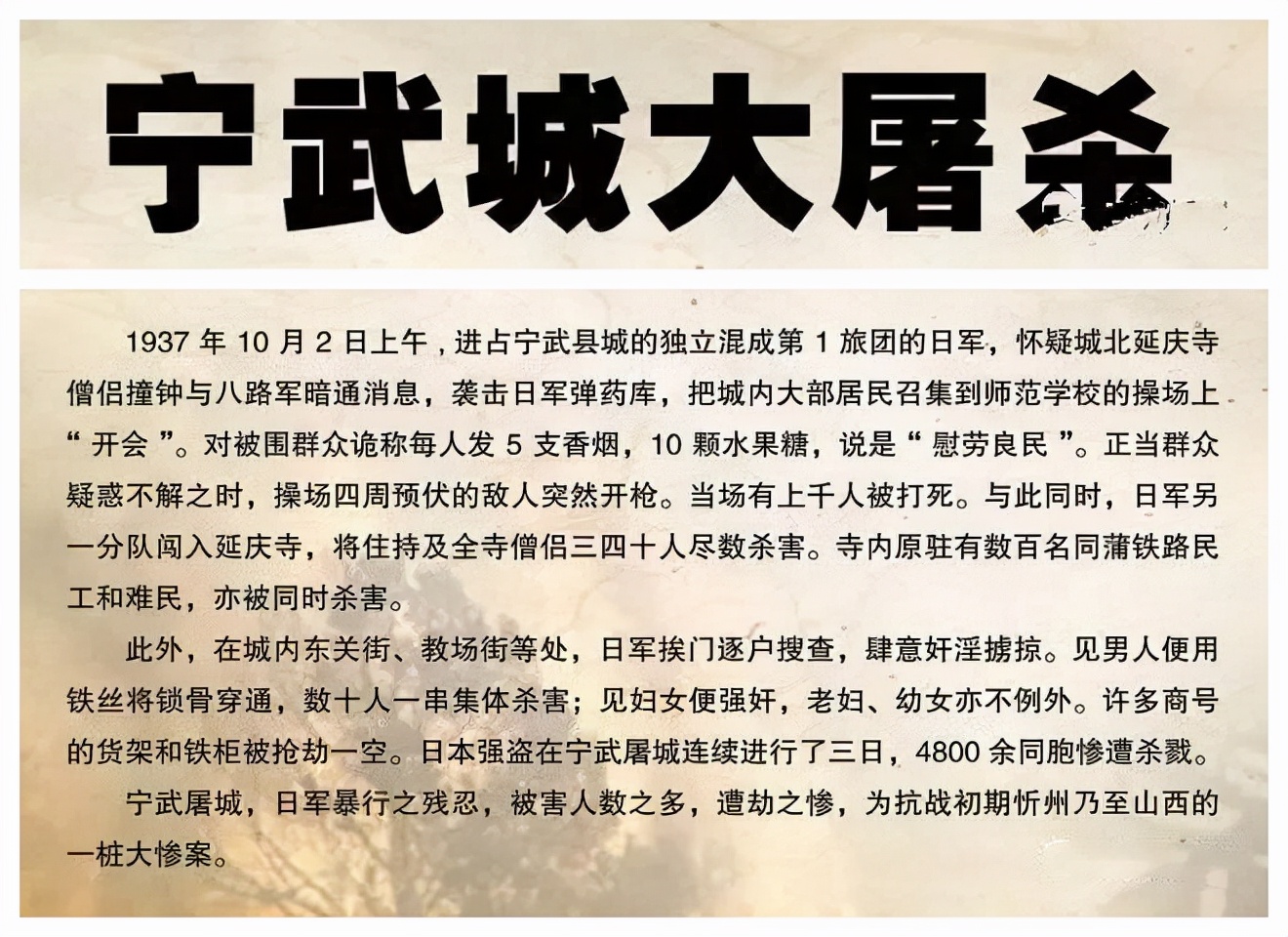五桂山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古氏宗祠)。记者 郭智军 摄
中山市槟榔山抗日烈士纪念碑。南记者 郭智军 摄
1939年7月至9月,日军两次向中山横门沿岸进犯,两次均被击退。横门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张气焰,拉开中山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图为日军进犯横门。姜术俊供图
《西行漫记》封面上这位吹冲锋号的战士,就是谢立全。记者 郭智军 翻拍
珠江纵队老战士冯永。记者 郭智军 摄
小隐乡最高民房被日军烧毁。记者 郭智军 翻拍
在横门保卫战中,日军一艘运输舰触爆水雷,当场沉没。姜术俊供图
站在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的小隐水闸上向东望去,不甚宽阔的横门水道,被横门岛分为两股,最终汇入大海。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郭昉凌说,由于城市发展,如今的横门水道相较于70多年前,已经窄了不少,就连小隐水闸也是在原处新修的。
1939年7月—9月,日军两次从横门水道入侵中山。“两次横门保卫战打得最为惨烈,国民党守军死了100多人,几乎没了一半。”郭昉凌说,当时中共中山县委也以“抗日先锋队”名义组成横门前线支前指挥部,并组建武装和国民党守备总队并肩作战。在国共两党联合抗击下,日军的两次入侵均被击退。横门保卫战两度告捷,大大鼓舞了中山人民的抗战信心。
三灶惨案
日军5天内屠杀逾千人
1937年8月9日,日军侵占中山七区荷包岛,是为侵犯中山县境之始。1938年2月16日,日军占领七区三灶岛(现属于珠海),在岛的南部修建飞机场,把三灶作为侵略华南桥头堡。
《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历史》记载,1938年3至4月,日军的三灶飞机场工事建成后,就把从朝鲜、台湾、东北及万山、横琴(今属于珠海)等地抓来的3000民工全部杀害。不甘屈辱的三灶人民拿起武器与日军抗争,日军当即在三灶施行“焦土政策”,短短5天内杀害岛内居民逾千人。当年5月4日傍晚,日军飞机在中山县城进行第一次空袭。
103岁的蔡槐对77年前的经历记忆犹新——
1938年农历三月初十,一队日军来到蔡槐所在的村子,要发放良民证。躲到山上的村民听说可以领取良民证,都纷纷下山了,不料日军突然变脸。两天之后,日军从月堂、鱼弄等村子抓来380多人,从中挑选出青壮者30多人,强迫他们在关家祠堂门口的田中挖出一个长宽各3丈,深约7尺的大坑。随后,日军把村民拉到田里,30到40人编成一队,击毙一批又拉一批过去,死了的就往坑里推。
当时26岁的蔡槐也被拉出去,幸运的是,他的手脚并未被绑紧。“我周边都是人,日本兵一开枪,我就挣脱绳索迅速逃到芦苇塘里藏起来。”日军的杀人行为持续到晚上9点左右,然后放火烧尸体,烧了半个多钟头。380多人中仅有几个死里逃生,蔡槐一家几十人都没有了。
抗战胜利后,三灶人民将死难同胞尸骨搜集埋葬。1948年,华侨捐款在上茅田村建了“万人坟”。1979年,当地华侨捐资,将坟迁至对面竹沥山新址,修建了“三灶岛三一三死难同胞纪念碑”,这是广东省内罕见的日军侵华罪行遗址。据中山县志记载,1934年中山的人口为116.8万人,1943年为74.47万人,锐减36.24%。
横门保卫战
拉开中山抗日斗争序幕
1939年7月24日,日军出动舰艇,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向中山横门沿岸进犯,国民党中山县守备总队三个大队九个中队的官兵奋力抵抗。其中,共产党掌握的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也冲上了前线。
中共中山县委成立了横门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全县抗日先锋队、妇协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男女组成宣传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等,到前线做后勤工作,还从各区抽来抗日先锋队武装队员,组成100多人的武装集结队。
久战不下,7月30日,日军只能撤退,日军一艘运输舰在仓皇撤退中,于玻璃围附近触爆水雷,当场沉没。首次横门保卫战打了8天,击退了日军。当年9月7日至20日,日军再犯横门,守军与之激战,毙、伤敌兵200余人。第二次横门保卫战又苦战了14天。
“打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做饭、烧水,全民抗战。”郭昉凌说,第二次横门保卫战,日军海陆空全部出动,轰炸很厉害,抗战群众的武器很落后,“打几枪,枪管就软了,子弹打不出去”,不过全民抗战的热情都很高涨。
两次横门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不可战胜”的嚣张气焰,拉开中山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在时任中山抗日先锋队总务部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欧初看来,这场胜利不仅保卫了家园,还增强了民众抗日的信心。“对海外也有深远的影响,让侨胞们知道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定决心。”
游击战
令日伪军胆战心惊
兴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古氏宗祠,如今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一进门,墙壁的一面挂着“珠江纵队挺进各地路线图”,另一面是纪念抗战英雄的浮雕。正对大门是一幅巨大的油画——中区纵队成立大会,那一幕发生在1945年1月15日的古氏宗祠。村内老人告诉记者,宗祠内的布局和当年司令部的布局一模一样。这里是当年珠江纵队司令部活动的地方。
据中山党史办主任黄春华介绍,1943年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日渐稳固,南番中顺游击队指挥部从禺南转移到五桂山。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期间,中共先后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中区纵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抗战期间,珠江纵队及其前身由几十人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岭南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各地的武装队伍结合当地阡陌纵横、河网密布的地理特点以及敌强我弱的形势,巧妙运用袭击战、麻雀战、爆破战、地雷战、海上游击战等,让日伪军胆战心惊。
因不满日军暴行,当时中山不少年轻人瞒着家人投身革命,老兵冯永(见右图)就是其中的一个。冯永是中山县五区翠微村(现属珠海)人,原本随父亲在香港念高中,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被迫回老家种田。前山是冯永卖菜的必经之路,那时已被日军占领,有日本兵站岗,过往的行人必须向他们鞠躬敬礼,稍有不慎就会被打耳光,甚至提枪杀人。“我也被扇过两次耳光,眼冒金星,人都快晕了。”冯永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自身的屈辱经历加之耳闻目睹日军烧杀抢掠的恶行,让冯永觉得应该做点什么。1944年5月的一个晚上,他和同村几个年轻人一商量,决定去加入五桂山的部队。“我简单收拾了两三件衣服,就到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白马中队,打日本鬼子去了。”
欧初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记载,仅1944年10月至1945年,珠江纵队一支队经历较大战役9次,拔除敌伪重要据点7处,消灭敌伪9个中队,缴获炮2门,机枪7挺,长短枪140支,以及粮食、弹药一大批。
1945年日军对五桂山地区进行扫荡,攻入游击队指挥部的日军驻扎槟榔山,对五桂山人民实行“三光”政策,日寇还放火烧了槟榔村的珠纵司令部以及侨眷谢嫂的房子。敌人扫荡期间,珠纵一支队16位战士来不及转移,藏在大托山腰的炭窑内,7天7夜未进半点食物,后被扫山的敌人抓获。
日军将16位战士拉到石莹桥后山的一块大石旁,游击队员们宁死不降,残暴的日军就将他们推倒在大石上进行碎尸,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溪。1993年,当地政府在这块大石头旁修建了抗日烈士纪念碑。(记者 李梦瑶 邓泳秋)
■对话
斯诺《西行漫记》封面“号手”谢立全之子谢小朋讲述其父抗战事迹——
周恩来亲授化装技巧 假扮商人智擒“飞天鸭”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上,一位英姿飒爽的战士迎着朝阳,精神抖擞地吹着冲锋号,这位战士就是谢立全。
1940年,带着党中央交待的历史使命,谢立全机智地闯过敌伪的道道关卡,长途跋涉到达珠三角。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心县委广州市第二游击支队特务中队教官、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等职务,倡议并领导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代表中心县领导中山敌后游击斗争,指挥战斗200多次,屡屡获胜。南方日报记者近日辗转联系到谢立全之子谢小朋,并进行了采访。
斯诺邀拍“号手”照片
南方日报:说到您父亲,不得不提到斯诺那张著名的“号手”照片。这张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谢小朋:事实上,父亲为人很低调,也不常和我们谈起过去的战斗经历以及生活。唯独这张照片,勾起了他对难忘的战斗岁月的回忆,于是就提笔给我母亲写了一封关于照片拍摄经过的信。
其实,我父亲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当时斯诺打算拍一个号手的形象,父亲因为体格健壮、身挎手枪,被一眼相中了。最主要是因为他身上那套当时并不多见的新军装,那是他刚刚指挥了一场胜仗、上级奖励的奖品。这个秘密被我们家珍藏了整整24年,直到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筹拍一部专题片,摄制组重走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县烈士纪念馆发现了照片和父亲写给母亲的那封信的影印件,才被公开的。
不断变换身份一路南下
南方日报:当时您父亲从延安受命前往广东,这一路是怎样通过敌人的检查?
谢小朋:父亲南下广东一路,克服了不少困难。路过重庆时,周恩来还亲自传授他化装技巧,为了不被敌人拆穿,临出发前,他要求父亲交出党证,父亲很不舍,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只好从了。一路上,父亲曾伪装过商人、国民党军官等,穿越重重关卡来到广东。在广东打游击时,因他是江西人,一开口就会露馅,所以平日里都装成哑巴到各处收集情报。
说起父亲“高超”的化装技术,还有许多故事,其中一个活捉“飞天鸭”的事情,我到中山走访时听一些老同志说起。“飞天鸭”郑东镇是三乡群众痛恨的汉奸“地头蛇”,但他很狡猾,为了摸清他的情况,父亲多次化装成商人到茶楼饮茶,仔细观察郑的特征,连郑家有地道的情况也一清二楚,后来在擒拿郑东镇的战斗中,他率主力部队攻入郑宅,却不见郑本人,这时发现有人打开地窖逃跑,父亲一眼就认出,这个十只手指戴满金戒指的人正是郑东镇,当场活捉了“飞天鸭”。
出书稿酬接济烈士家属
南方日报:在广东指挥游击战斗的这段经历,您父亲向家人提起过吗?
谢小朋: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等职。尽管战斗经历不常提起,但作为子女,听到最多的是他对第二故乡——广东的思念之情,念念不忘老百姓对抗日武装的支持,甚至期望战胜癌症之后,退休回到广东。十年前我曾到过珠三角,当地干部群众称呼我父亲为“老陈”、“陈教官”、“胡须陈”,从中就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和当地群众之间的感情。
我亲耳从先父口中听到过,当地群众一次又一次救过他的命。有一次,父亲遇到日伪军盘查,他立马把左轮枪插进水稻田,混在农民中弯腰插秧,群众也自发地将他挡住,帮他化险为夷。
而让他甚为得意的是,在珠三角水网各村群众中设立了多个秘密据点,囤积粮食弹药。每次战斗之后,就会有老百姓划着小艇,或带路穿过甘蔗地,将游击队送往下一个村庄休整,在日军重兵集团面前来去自如,孙中山先生的亲属都接济过部队。
南方日报:您父亲对广东充满着感情,解放后还有与战友联系吗?
谢小朋:有的,父亲对当地人民、对烈士遗孤非常关心,舍得花钱为他们解决困难。我们家的钱主要有两大支出:父亲尽量让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吃好;其余的钱大部分被他定期接济阵亡战友遗属了。我还记得,1961年他的《珠江怒潮》一书出版,当时稿费有3000元,除了给我哥哥买了一块手表外,其余的钱都送给广东西海他原来战斗过的地方的一位烈士家属,接济他们的生活。父亲在世时,和我提起过广东烈士杨日韶的母亲杨伯母,杨日韶牺牲后,他的母亲强忍悲痛,变卖家产支援游击队,还将小女儿送到部队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也曾到中山探望这位革命母亲。
■故事
中山南朗镇关塘村妇女陈雁群:
日军眼皮底下掩护同志脱险
中山沦陷后,不少爱国群众将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掩护部队活动,救护伤病战士。家住南朗镇关塘村东桠大同街的陈雁群就是其中的代表。陈雁群虽是一位农村妇女,却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大力支持女儿和细叔参加抗日先锋队,鼓励年幼的儿女参加抗日宣传,自己则积极参加“战时妇女救国会”工作。
中山抗日游击队大队在五桂山成立后,在合水口村成立交通总站,下设多个分站,代号“白鸽队”。陈雁群家作为“白鸽队”的重要分站,主要任务是传送情报和部队信件,运输枪支、弹药、药品,掩护游击战士、干部和伤病员。游击队的同志到东桠村开展秘密活动,都会先到陈雁群家联系。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经常在黑夜从屋后山坡翻过后墙,登上碉楼,由陈伯母安置好休息。陈雁群宁可让家里人少吃省用,也要让伤病员吃饱、睡好,早日康复归队。
1943年6月初,日伪军兵分几路围攻五桂山游击大队,其中一支日军分队驻扎在东桠村,住在临近的小学校舍里,还将陈雁群家的客厅霸占,作为开会、指挥的场所。而此时,她家碉楼三楼上刚好就隐藏着游击队的伤病员。形势非常危急!
为了麻痹敌人,陈雁群一家人装作若无其事,像平常一样进进出出。她的儿子温大川当年只有13岁,虽然心中对敌人甚是憎恨,但为了掩护游击战士,却还得装扮成很友好,在日本兵中周旋玩耍,最终让碉楼里的游击战士安然度过危险。
(感谢中山市政协主席丘树宏、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郭昉凌对本文的支持)


![日本兵“战地日记”再现日军侵华暴行[组图]](https://www.66613.net/d/file/p/2024/01-17/61f5b2cb98fda612645ca0d73602de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