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许老师,您好!您从山东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讲坛八年之后又师从徐苹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城市考古的研究,直至现在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您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能否回顾一下您的研究历程,尤其是研究三代都邑文明的心路历程?
许宏老师: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用“中国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探索”来概括。主要的着眼点是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和社会复杂化。其中“三代都邑文明”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1984年本科毕业留校时,研究方向就定在先秦。先是当辅导员,做学生管理工作,现在想来也是一段难得的历练。同时给讲新石器考古的老师当助教,准备幻灯片、辅导学生。当助教时又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做的是山东地区的商代文化;攻读学位时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89年硕士毕业,同年领队培训班结业。第二年拿到了个人考古领队资格,提上了讲师。这期间多次带学生实习,发掘的是出有陶文的丁公城址,遗存属于新石器到商周这一段。后来因教学需要给学生上过《战国秦汉考古》课。专业领域上看都属于中国考古学的前段,这就是我在山东大学任教八年的经历,回想起来趁年轻还是干了不少事儿,挺充实的。从新石器到东汉考古的学习、发掘、教学和研究,初步奠定了日后业务发展的基础。
1992年到我们研究生院读博士,师从徐苹芳教授,专业方向是城市考古。徐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历史时期考古,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但是徐先生是一个贯通的学者,他任所长的时候组织召开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两次研讨会,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我和徐先生商量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先生说既然你的学术背景是前段,那么你就做先秦城市考古吧,研究下限就定在战国――写中国的前帝国时代。这样我的学术积累就全用上了。论文涉及范围从社会初步复杂化的仰韶时代后期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课题研究的上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战国,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里,要把中国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这么大一个主题梳理清楚。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四年之内(中间去日本研修一年,眼界进一步开阔)努力为之,论文也就做了出来。这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也就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让我对早期中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
1996年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所里把我安排在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搞的还是早期中国。我个人本想避开精兵强将成堆的夏商考古,专攻东周考古,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太重要了,而所里基本上没人做。领导从学科布局上考虑也认可了我的想法,于是我接下了同仁们视为畏途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的“周代墓葬”部分,准备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东周城市是我博士论文中的重头戏,如果把墓葬再熟悉起来,这一块基本上就可以驾驭起来了。
当然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安排。那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阶段,王巍所长(当时是我们室主任)带队大规模发掘偃师商城宫殿区,我也受命作为“机动部队”的一员临时借调参与会战。没想到一干就是两年半的时间,五个季度。白天发掘,晚上和业余做东周墓葬的卡片。凭着以往的工作基础,我一个人负责1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带几十个民工,手下只有一个技工,田野图都是自己画的。到最后一个季度,王巍先生升任副所长,于是责成我作为执行领队,完成了最后的发掘任务。两年半下来,手写的发掘记录达数万字。正由于这段经历,我与夏商考古,与河南偃师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从三代考古的尾端东周,跳到了三代考古的开端――二里头文化。这倒真的和在大学当教师、做博士论文一样,让我从二里头一直到战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而不是限于三代中的哪一段。

初雪・二里头
接手二里头,我知道自己最大的不足是对于二里头文化和大家习称的夏文化没有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但同时这可能又是有利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因为没有研究,没有参与关于夏文化和夏商分界问题的讨论,没有观点也就谈不上偏见,所以我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和问题意识来的,边思考边做,边做边思考。
在关于二里头的族属和王朝分界的问题上没有观点,本身就是一种观点。我的想法是,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学界最需要我做的,不是积极地参与论战、成一家之说引领风骚,而是尽快地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更翔实、更系统的考古学基础信息。我是学城市考古的,研究的是聚落形态,而学界争议了数十年的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并不清楚。我当然要从这一问题入手,来做二里头了。于是二里头有了准确的现存范围和面积,有了城市主干道网的发现、宫城的发现、带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围垣作坊区的发现、绿松石器作坊的发现、车辙的发现,等等。就二里头都邑的王朝归属来说,这些收获并没有直接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了更多新的、可以引发学界思考的问题。这些发现,正是可以显现考古学的强项的地方。暂时不知道它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影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份量的把握。

在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
总体来说,我的研究领域可以分成这么几大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市研究,文明、礼制与国家形成,以及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一个学者的研究要有点有面,既深且博。作为一个出身于田野的考古学者,田野是立身之本,我个人的这一个“点”就是二里头,从这里钻进去,力争吃透,进而“感知早期中国”。“面”则是与其相关的城市、文明、礼制、国家,衍生出的副产品就是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坦率地讲我几乎没有系统地读过纯理论的书,这些思考都是出自于田野的实践,一边发掘,一边思考。不甘沦为发掘匠,不敢成为思想家,起码要是个思考者吧。
看你们的采访提纲上总希望对青年学者提些建议,或问及要加强哪方面的训练,我觉得上面这些偶然和必然相混杂的人生经历及切身体会,可能已经给出了些许答案,不敢好为人师,就不单独谈了吧。
知道自己天分并不高,于是崇尚的人生信条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记者:作为二里头队队长,您和您的队友们一起发掘着“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已经有了这么些重要的发现。这些发现比如宫城您曾说是“想”出来的,通过二里头以及其他遗址这么多年的发掘,您对考古发掘有什么体会?
许宏老师:前面说到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先秦城市考古,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就得到了一个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我在工作中,是把二里头放在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的。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的发现等,都得益于若干学术理念与构想,而这些理念与构想,都要溯源于在徐先生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时的思考与收获。
比如二里头的宫城,就的确可以说是“想”出来的。
统观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沣镐遗址都没有发现城墙。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汇报二里头遗址发掘情况
著名的二里头1号、2号基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位于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勘探结果表明,2号宫殿东墙外侧紧临大路,大路以外只见有中小型建筑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号东墙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宫殿区的东部边界。而二者之间已不可能有墙、壕之类防御设施存在。鉴于此,当时我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如果宫殿区围以垣墙,那么早已发现的2号宫殿基址的东墙有可能就是宫城城墙。
在二里头遗址这样持续兴盛数百年且遭后世严重破坏的大聚落上,用洛阳铲进行的钻孔勘探仅能提供些微线索,而无法摸清地下遗存的详细情况。对上述推断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先揭开2号基址东北角,看看2米宽的宫殿东墙夯土是否继续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正当肆虐全国的“非典”来临之际,发掘工作按这一思路开始实施。当在新揭露的探方中,与2号宫殿东墙完全一致的条状夯土果真象上述推想那样向北笔直地延伸时,你可以想见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暗喜。为什么只能暗喜呢?因为这还不能排除它是2号基址以北又一处院落的围墙。那就要看它在2号宫殿东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于是我又安排揭开2号基址东南角及其以南区域。当得知同样是 2米宽的夯土墙继续向南延伸的时候,欣喜之情才溢于言表。于是我们又向北向南一路追探,并开探沟解剖加以确认。这样,到了春夏之交,这道夯土墙可确认的长度已近300米,可以肯定属宫城城垣无疑。
伴随突发事件的复杂心灵感受与面临突破性发现的兴奋心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2003年春我和我的队友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甚至要感谢“非典”,当时中国农村的“严防死守”让我们减掉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更专心于扩大我们的战果。
此后,我们又乘胜追击,一举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至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宫城被揭露了出来。
由是想起早年苏秉琦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的一句话。记得苏先生话的大意是: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挖到什么。这让专攻考古学的我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的想法是这好像有点“唯心”,在以实证为特征的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讲不通。在经历了多年的考古实践后,我逐渐意识到了这句话的份量和真谛之所在。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与邹衡先生在二里头遗址
记者:许老师,您的博客现在是我每天的功课。我们除了读您的文章,还有就是通过您的博客了解您。您的博客对专业人士和大众来说,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为大众了解考古提供了一种途径,您开博客的初衷是什么?博客开通这么久,很受大家的喜爱您有什么感触?
许宏老师:开博客源于一次访谈的触动。
我们研究生院的一帮校友,在母校建院三十周年(即2008年社科院研究生院30年院庆)时想做点事,决定为母校编本书,就想到了《三十年三十人》这样一个题目。于是在研究生院的毕业生中,各行各业之间找30个人做访谈,考古这行就找到了我(《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中信出版社,2008年)。这本书的编辑有研究各个专业的。访谈之后,他们看到了考古人的思考感觉很兴奋,说大家的思考是共通的。作为“封闭”了太久的考古人,其学术思考能为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所认可,产生共鸣,这让我从外界评价的角度,意识到我们这个学科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原来讨论的内容一旦上升到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上升到人和社会的层面,每个学科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考古人这样的思考,应该让更多人了解,与他们分享。
开博客之初,只是想把已经发表的文字贴上去,算作成果的电子本,让大家找起来、用起来方便。时间渐长,有网友跟贴提问题,有些问题是很具有启发性的,也就开始试作回答。圈内朋友的问题还比较容易回答,犹如回答什么是水桶这样的问题,但是回答什么是水,就很难了,就涉及到学科的本源问题了。你必须用准确的学术术语来回答,这也是激发刺激自己思考的过程。如果是一篇论文我可能翻来覆去不肯下笔,但这个问题就一句话,一个概念,你为“小朋友”们讲明白,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也富于挑战性。
我觉得博客还有一个好处是弥补了我现在没有做大学教师的遗憾,因为我乐于和年轻人交流。尽管我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多,和学生交流的机会也少。而在博客上主要是和年轻人交流,博客上的交流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因为是师生,他们见了面会很谦恭地喊我“老师”,我若说点什么想法,他们就会连声附合“是是是”。我就怕这样,这未必是他们真实的观点。而博客里面他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甚至批评我,反正是隐身。这是朋友间的交流,这种感觉我特别珍惜。我觉得最大的快慰就是年轻人把我当朋友。坦率地讲,当目前学界主流意见与他们的看法相左时,我更看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我们学科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我也以我的观点得到他们的认可为荣。
有位朋友说我博客的主题是“学术与人生,历史与思考”,我觉得比较恰切,这也是我个人的定位。作为一个中年学者,以前认为学术是学术、人生是人生,为了学术可以抛家舍业,无暇他顾,现在有一种学术和人生融为一体的感觉。其实学问、工作、家庭、亲情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做学问则重在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要一门心思地达到一个什么顶点。现在是这样一种通达的感觉。
一个庸忙的中年学者,何以爱上了博客?我也在问自己。 可以用我博客上的一篇博文《爱上博客的四大理由》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自娱自乐的感觉
作为已远离了农耕的农耕民族的传人,尝到了侍候自家菜园子那一亩三分地儿的快感。
尝到了暂时不受制于人,自己当编辑、自主组稿、自主排版、随时签发的快感。有朋友说我适于当编辑,这辈子没当成,颇引以为憾,这下过了把瘾。
同时,对于一个庸忙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生活的调剂,一处精神家园。
二、练笔和刺激思考的功效
这二者相互作用,在切磋琢磨中进步。原本艰涩凝滞的笔触逐渐变得轻快起来。这显然大大有利于治学。
三、交流的收获
在与以青年为主体的博友的交流中,不断校正、纠偏自己的“抛砖”之论,不断完善自己的思考。
这里没有身份地位之别,没有长幼大小之分,没有圈内圈外之歧见。隐身的博友们没必要恭维,尽可以批判。平等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的碰撞让大家共同受益。
四、分享的快慰
转瞬即逝的灵感火花,尚无法成文、正式发表的想法,邂逅的妙文佳句,都可以“保存”在博客上,让博友咀嚼分享,收获同感和共鸣,或者批评与异议。这是存在于纸面和会议上的学界氛围所无法比拟的。
有这样的收获,何乐而不为?
记者:恭喜您的新书――《最早的中国》面世,您能谈谈这本书的创作缘起和思路吗?
许宏老师:我在偃师活动(注:即于2009年8月29日~30日举行的“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公众考古活动,活动内容详见中国考古网)开幕式暨这本小书的首发式上,曾有一段作者感言:“这本小书,与其说我是作者,不如说我是执笔者,这是五十年间几代人,通过辛苦踏实的工作结下的一个果子。二里头遗址发掘迄今五十年,以往关于她的书都是面向学术界的,而这是第一本写二里头、又面向公众面向文化人的著作。所以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果”。我现在仍想表达深深的感恩之情,任何成果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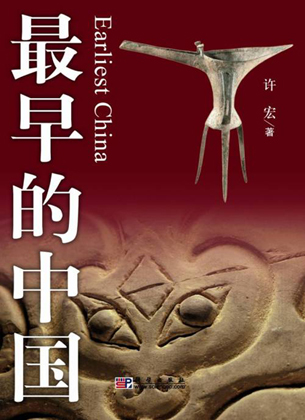
具体说到这本小书,其实是被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闫向东社长,在2006年初冬用一份午餐盒饭及此后的不断激励“哄”出来和“逼”出来的。我与闫社长的一个共识是,这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学术著作。说它是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是学者秉持“有一说一”的学术原则写就的。但它又是一部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众而非仅为学界的学术著作。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它能让公众,尤其是文化人愿意看,读得进去,读得不累,甚至读得畅快。
作为考古界的普通一员,我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学科的这种转变。
如果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史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这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者也开始了将文物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产品的尝试。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王仁湘先生主编、由考古学者分头执笔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就曾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20世纪最佳文博图书,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但这些努力与业绩似乎没有对我这个自认为偏于保守的学者产生太大的影响。记得1996年《读书》杂志曾特约数位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来讨论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几位学者直陈对考古学话语系统的疑惑、慨叹和望而生畏。其中我的同事陈星灿先生的文题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读了之后尽管颇以为是,但当时的想法仍然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不满于充斥坊间的考古大发现类的“攒书”,一方面又不肯或舍不得拿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公众考古的行列中来,这基本上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考古界相当一部分同仁的心态。
因此,当2006年闫向东社长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能考虑写一本向文化大众解读二里头的小书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婉言谢绝,当即答曰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是考古报告,而我正在编纂二里头的考古报告。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起来时,当我以此为契机开始全面梳理前辈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探索历程,开始从比较文明史的宏阔视角来看二里头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国”,开始试图发掘一件件文物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时,我已经不把这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学者的一项副业,它已经成为我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逼着我又读了许多书,搞清了不少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我进一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增长点。这种感觉王仁湘老师曾告诉过我,现在我自己体会到了。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了不安,但同时也充满了收获与思考的快慰!
本书的成稿,可以看作是考古人努力面向公众的一个青涩的果实。说其青涩,绝非谦辞。对于学者来说,写一部学术专著并非难事,但写这样一部不同于以往概念的学术著作,他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可想而知的。在被闫社长调动起积极性的“兴奋”之后,是一种忐忑,及至小书面世的现在,又有一种释然的感觉,不管读者对它的评价如何。毕竟,作为考古人,“自觉”地走出了这一步,就我个人而言,这本小书的写作也因挑战自我而可以看作是学术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
一直有朋友和学生说我对自己所挚爱的考古事业,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富于激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激情,才使我最终被闫社长说动,产生完成这本书的冲动。这本小书,也不过是我作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主持人,对二里头遗址的一种解读而已。换句话说,它展现的仅是我眼中的二里头,一个使我兴奋的“中国”的存在。勿庸讳言的是,我当然也希望读者在看了关于她的故事之后,也为二里头这个中国乃至全球文明的硕果而兴奋。我自己给这本小书的定位是:以二里头为切入点,实说、精说和深说“中国”诞生史。但是否做到,就要读者来评判了。至少,这本小书中包含了对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历程的再认识,读者诸君从中可以了解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的“中国”的由来。
闫社长当时说我这本书的出版会具有示范意义,因为像我这样自认为偏于“保守”的学者如果都能写出这种面向公众的书,会鼓励一批长期奋战在考古第一线的学者积极跟进。这本小书如能起到这种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是我至感快慰的了。
记者:我们熟悉夏商周考古的学子都能感受到您对二里头的热爱,近期您和刘国祥研究员合作主持的“走进二里头 感知早期中国”公众考古活动反响很好。活动设有专业学术论坛和公众论坛等,活动设计既具有专业性,又贴近公众。首都博物馆刚结束的《早期中国》展获得了多方的赞誉,听说您在策划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考古正在走出象牙塔,向大众普及,体现公众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专业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或责任?
许宏老师:我们的学科积淀到了这种程度,个人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也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可以说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了出来,觉得作为学者,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回馈社会了。

“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之向公众讲解二里头文化
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诞生伊始,本来就是因应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乃至国际学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近百年来,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必须从田野实践的精微处做起。整个学界花费了几代人的精力,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由于专业的特点,譬如田野操作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追求作为现代学问的科学性等等原因,考古学必须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来解读这部无字天书。随着大量材料的爆炸式涌现,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逐步细化,使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考古学给人以渐渐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与这个学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史学家也常抱怨读不懂考古报告,解读无字天书的人又造出了新的天书。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问题,考古学的成果已开始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考古学者也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

“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之与公众互动
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这种提法似乎偏于“致用”的考虑,但细想起来,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从接受访谈谈考古人的思考,到写作出版面向公众的《最早的中国》一书,到组织公共考古活动,参与大型展览的策划,贯穿其中的都是这种被唤起的社会责任感。我愿意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获回报社会。
记者:你们研究室主编的《三代考古》(三)已经出版了,读者们注意到第三辑的风格有一定变化,体现了你们新的理念,你们室还有其他发展规划吗?
许宏老师:如果说《最早的中国》是学者本位的个人研究成果的话,那么组织对《三代考古》文集的编纂,就是我们在学科建设理念上的一个实践。我们请两位老主任――王巍先生和杜金鹏先生来当我们的主编,给我们把关定向,具体的事我们来做。前任主任杜金鹏先生对文集的创立有筚路蓝缕之功,用我们上一阶段的重点学科经费,打造了这套文集。杜金鹏先生在任时出了两辑,我们这个班子开始编第三辑。形式上看分了板块,开始约外稿;内容上看,主流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相结合,研究论文与专题笔谈相结合。作者群上则资深学者与青年学者相结合,所内学者与所外学者相结合。所谓老中青三结合,海内外共研讨,鼓励思考,鼓励探索。不同的思路和角度相互激荡,不同的方法与观点交相辉映。其中,我们组织的学术考察活动笔谈“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板块,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两年来在文集的编纂上花了不少功夫,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当然其中肯定还有很多很多不足,因为精力实在有限。我们希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将《三代考古》丛书办成整合三代研究、展现学者风貌、增进学界交流、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学术平台。

说到发展规划,当然还有不少想法。
我们是院里重点学科创建活动入围的第一批研究室。建设重点学科与研究室的两大目标,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而重点是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我们研究室现有业务人员19名,基本上是30-50岁之间的“生力军”,他们活跃在田野第一线,同时也有较强的研究能力。这是夏商周考古研究领域最大的一个团队,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作为这个团队的“班长”,我特别珍惜我们这个团队。
出成果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田野工作收获。现在我们有5个都邑级的大遗址在开展工作,在学科转型、对田野工作方法提出新要求的情况下,如何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确保田野工作质量,最大限度地提取各类用于整合研究的信息,并贡献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这方面我们将进一步集思广益,统一协调,抓紧抓好。
出成果的第二个方面则是综合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主动性发掘趋向缩减的形势下,提高科研能力,加强综合研究,成为全室同仁的共识。《三代考古》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和交流的平台。
出成果的关键又是出人才,是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上,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提高层次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鼓励支持中青年学者走出国门、境外,进行研修、实习或访问,认为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尽可能为其开绿灯。近两年每年都有数名中青年学者在外研修和参加发掘。此外,我们还有计划地组织全室人员考察本室同仁及兄弟单位的发掘现场,考察相关遗址、观摩遗物,组织座谈交流,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另一个方面是给年轻学者加担子,创造条件让他们独立带工地、独立完成科研项目,充分调动其积极性,通过“放飞”促使其尽早成熟,争取顺利接班。
目前,我们的田野工作存在摊子多、人手少的矛盾,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立重点课题,避免平均用力,集中优势兵力完成重要的学术任务,这一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即将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中,我们负责的陶寺和二里头两大遗址是攻关的重中之重。相信我们这个团队将在应对机遇与挑战中踏实前行,取得更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孙丹)





